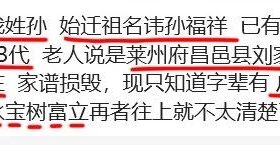疫情在家的时候,师兄们牵头建了一个昌邑一中的青岛校友群。有次在群里聊到高考,我说,分数公布那天,我正在村南的河里领着一群半大小子“下河”来。

快晌午,俺嫲嫲踮着小脚来喊我:快回家吧,分数下来了!我说多少分?好像是690多分。哈哈!本科了!(因为前一年的本科线是650分)我一高兴光着屁股就上了岸,不管俺嫲嫲在后边怎么喊都听不见,边穿衣裳边往家跑。
这是1997年的夏天。今天又是高考,回想23年前,我经历的高考,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很具喜感的画面,颇有点范进中举的意味。
我的“癫狂”源于那年我的超常发挥。因为俺爹在高考前,特意跑到城里,跟老师询问我的情况。俺老师有点为难,说,考个专科就不错了。这是我考上以后俺爹告诉我的,我并没有在场,但我能想象出望子成龙的他,当时会有多失望。

都说,考上一中一只脚就进了大学。我却是那类想把脚再迈出来的学生。我当时进一中是全校第九名,但三年下来,我竟然混到了一个文科班的20名以后。其间的种种厌学、叛逆、混账和不服管教自不必赘述。大多像我这样,进一中时成绩很好,高考平平甚至落榜的同学,几乎都是这样的成长轨迹。
一中的张校长也在青岛校友群里,建议他研究研究,别让小师弟师妹们再重蹈我们这些典型样本的覆辙。当然这是题外话,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,我最终能考上本科,确实走运,是“祖坟冒了青烟”。
1997年的高考是什么样子呢?我使劲搜罗残存的记忆,拼出一些片段。
那年夏天好像特别热,感觉校门口青年路的沥青,都要被晒化了,四层的教学楼门窗全都敞开着,教室里散发出热气腾腾的备考气息,只有楼下的音像店,单曲循环着“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,从分手的那一天,九百九十九朵玫瑰……”是的,这首歌我做梦都会唱,一直到现在都是我去ktv的保留曲目。

高考前,为了给我增加营养,俺娘把每月的10元零花钱,提到了50元,叮嘱我每天买点鸡蛋和牛奶吃。我从小喜欢麦乳精,讨厌奶粉和一切奶制品,结果增加的伙食费,都去校门口买了鸡腿面包,还有去大棚吃了肉火烧和廷富拉面。直到现在,鸡腿面包和琵琶梗还是我的主要点心,以至于女儿常常笑话我:妈妈快看,爸爸这都是吃的啥零食啊!
高考在稀里糊涂的复习中来临了。我被分到了城后职业中专考场,我记得在二楼,座位是一进门靠墙的第二个。1997年的高考,声势没有如今的浩大,没有拉起的警戒线,没有警车开道,也没有鲜花和穿旗袍的女家长。仪式感不足,但同样备受全社会瞩目。考点门口也是围满了焦急等待的家长们。俺娘怕我在学校吃不好,高考那三天特意借宿到城里的一个婶婶家里,每次考完试都接我去吃饭。我的超常发挥,应该有俺娘一半的功劳。
俺爹说,没能参加78和79年的高考,是他一辈子的遗憾。因为恢复高考那两年,我的几个姑姑都已经出嫁,家里还有一个精神失常的大爷,如果他去上学,丢下俺嫲嫲和大爷在家,没人劳动挣公分,他们就没法生活下去。

俺爹学习很好,曾经找他辅导的学生和同事很多都考上了大学,他却因为家庭的负担,放弃了高考。不知道我那年的超常发挥,会不会弥补他心中些许的不甘。我也常常想起,那年夏天,母亲推着自行车伫立在烈日下的身影,后悔自己当时怎么那么不懂事,怎么会厌学,浪费了三年的大好时光。
无论如何,我还算幸运。挤过了高考的独木桥。记得小时候俺娘常跟我说,你如果不好好学,高中毕业就跟嫩大舅学木匠去。年少懵懂的我,只当那是句玩笑话。多年后我才明白,高考对于一个农家学子命运的改变:乡下少了一个小木匠,而城里多了一个码字工。
当然这种改变如今也难说孰优孰劣。
作者:继评,老家龙池,现居青岛,供职于大众报业集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