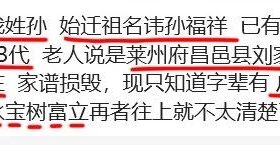父亲离去就要八年了。出门在外就是不孝!我在撕裂中撕裂着。每每想起父亲,唏嘘不已,思绪中的那年、那月、那些事缕缕如故萦绕心扉。
1931年阴历大年三十的晚上,一声啼哭划破了一个寂宁的农家小院。父亲的出生给这个小家带来了不少新年的气氛。父亲上面有一个哥哥,两个姐姐。爷爷、奶奶终于盼来了第二个儿子。据说,父亲小时候特别受宠,都五六岁了,大父亲十四岁的大伯,时不时地还背着父亲出去玩耍,两个姑姑对父亲更是喜爱有加。每逢过年、过节,奶奶分完小零食,还小的二姑也会随着大姑把父亲的衣服口袋装的满满的。那时,我们家的家境还算说的过去。爷爷种着地,还做着卖布的小买卖,奶奶又非常勤劳持家。可好景不长,父亲十六岁那年,二姑因病早早地离开了人世,奶奶也因病在那年去逝了。又是兵荒马乱的年月,村子里总有土匪来抓壮丁。体弱的父亲为了少让爷爷担惊和减轻家中的负担,放弃了学业和酷爱的绘画。就在这年,也就是1947年的秋天,踽踽独行,离开了家乡,辗转到了天津。

1950年的春节前,父亲在离开家的第三个年头,第一次回家,和媒说之言的母亲完了婚。当时,大伯家已有了三个哥哥,大伯母身体不太好。为了爷爷和这个家,过了年,父亲留下了新婚不久的母亲,独自回津。后来,大伯家的大哥该读中学了,父亲把大哥带到了天津,就读天津纺织机械技校。父母婚后的第四年,我大姑也因病去逝,留下了一个四岁多的女儿,这也成了父亲一生的挂念。
1963年的秋,年迈的爷爷去世了。送走了爷爷,父亲再想把母亲和两个姐姐带到天津,就很难上户口了。转年的10月份,有了我。父亲还是一年回来一次。不过,每年的冬天,母亲便能带着我到父亲身边待几个月了。尽管这样,在我五六岁的时候,我对父亲还是有陌生的感觉。 应该是1970年的夏天,父亲回来了。父亲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,做在庭堂的方桌旁,我怯怯的想靠近又不敢靠近,站在边上偷偷地看着父亲。父亲拉过了我的小手,把我抱到他的腿上,我才甜甜的笑着,喊了一声:“爹”,父亲自然也很开心。

转年,父亲是回来过的年。大年初二的早上,北风凛冽,大雪铺天盖地。中午时分,父亲终于在村口迎来了远道而来的大表姐。表姐是和同父异母的弟弟来的,一进门,父亲让姐俩做到了炕上,马上把挂着雪霜的布鞋放到了炉子的旁边烤着。父亲只顾着问长问短,表姐的鞋子被烤煳了。表姐看着过年才穿的新鞋,忐忑不安地掉下了泪。父亲有点不知所错,赶忙从抽屉里找来了麻绳,量了量表姐的鞋子。并安慰着表姐:“你先穿着,等舅回去给你买双新的”。小小的我不动声色地看在眼里。 父亲回津后,马上给表姐寄回一双鞋子,母亲谁也没让看,直接给表姐送了过去。这么多年,不光是我,就连两个姐姐谁都没享受过买鞋子穿的待遇,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在煤油灯下做的。
在我小时候的感觉里,我最不受父亲的“待见”,记得有一年父亲回家,给大姐、二姐每人买了一件条绒绵外衣。我看在眼里,喜欢在心里,用手摸摸,好想穿穿。父亲看在眼里:“你穿着太大”。却实,那时我太瘦小。可后来的一个夏天,父亲回来了,买了一快绿、白、黄间隔的涤棉布,给大姐、二姐、和大伯家新婚的三嫂每人做了一件短袖上衣,还是没有我的份,我心中有说不出的不快,不过父亲这次没有理我。一直到我上初中时,终于穿上了父亲为我买的第一件新衣服。我和大姐一人一件。可能是因为二姐已上班的缘故,这次没有二姐的份。当我穿上了带有银丝线的淡绿色的上衣时,所有孩提时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。
父亲有着细腻的一面。可急暴的一面令我毛骨悚然。记得外祖父去世的那年冬天。我又随母亲来到了父亲身边。母亲没经父亲同意,擅自买了一卷金纸、一卷银纸,想寄给我大姨母,让大姨母给外祖父扎点祭品。父亲看到后,竟然暴跳如雷,二话没说,把纸摔在了地下。我和母亲被父亲的举动惊呆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的火。母亲没有说话,把纸捡了起来。父亲看到母亲的沉默,只听父亲说:“死了孝不如活着孝,有这钱多给她姥姥买点吃的多好”。父亲这话并不虚伪。不管是父亲回家,还是母亲回去,父亲都会给外祖母买最爱吃的水果糖。我记的,每次我是能吃到一两块的,不过两个姐姐没有了份。在这方面母亲和父亲的口径是一致的:“孩子吃还早了,先济老人吃”。
到我父母老了的时候,我才真正地理解了父母的心。
早先,在我们姐三个当中,我跟父亲接触的时间最多,但我在父亲面前,还是很惧紧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,母亲炒了大葱炒鸡,父亲不动筷子我向来不能先动。父亲尝过后,就把盘子推到我的眼前,不过母亲不动筷子,我还是不敢动,等父亲发了话:“吃吧”,我才拿起筷子。后来,我懂得了父亲这是在给我立规矩。其实,这些年,也就是母亲和我到来后,父亲的生活才有所改善。平时,独自一个人的父亲对自己很苛克,从不在单位吃食堂和在外面买早点,都是下班后自己现点炉子现做饭,省下来的钱接济了家里的衣食住行。
父亲四十岁那年,得了胃穿孔,做了一次大手术,胃切出了三分之一,身体一直也没恢复好,母亲很是不放心。可我上学了,冬天再也不能和母亲到天津了。一直到我读初中,二姐上班住在了厂子里。冬天,母亲便把我交给了已婚的大姐,自己到天津照顾父亲。这时,父亲对我很奢侈,怕我上学远,为我买了一辆二六型飞鸽牌的昆车。这在当时,城市里都没有几个上学的孩子能骑上,何况那时的农村。这辆自行车,却实让我扬眉吐气了一次。
1983年我到了父亲的身边,父亲却实又让我很土气了一时。我一个弱弱的小女孩,骑着父亲给他自己买的,上海产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。这车是我还没到天津时,父亲就买了,一直没舍得骑。可一开始这辆车并没有给我带来欢乐,不光车子笨重,瘦小的我骑着这车,人也显的笨傻。心中有点蛮怨父亲。可看看父亲自己骑的、破旧的自行车,我越来越体会到了父亲那种有点不近情的爱。
小时候在母亲身边我没有人身的自由。从我到了天津,父亲却放开了我。可能是我大了的原故,也可能是父亲想落叶归根的缘故。父亲开始锻炼我在新的环境里生活的能力。从做饭、买粮、买菜、打水都让我独立的去完成。包括到同村的八大伯家,父亲的朋友家串门。父亲从不陪我去,而是划出线路图,让我自己去找。这对我一个从封闭的乡村刚刚步入喧哗的大城市的女孩来说,我感到了如此那般的不易。我比竟大了,理解了父亲的用心良苦。
在经济方面,父亲却没有给我自主权。我上班后的每一分工资都要交到父亲手里。应该是1985年,过年时,伯母轮到了二哥那里,大伯已不在了。父亲瞒着我给二哥寄去三百元钱和一件军大衣。过了好多年后,母亲跟我透露了这件事时,我没当会事。母亲笑了:“这钱可有你挣得,你没有怨言?”我只是摇摇头。其实,我知道,从1963年爷爷去世后,就分家过日子了。母亲带着我们姐仨,那时也不好过,家中的累活是伯家的哥哥们帮衬着。在经济上父亲一直都在接济着大伯一家,包括大伯给哥哥们盖房子,取媳妇。大伯去世后,伯母也成了父亲的牵挂。
父亲的所做在潜移默化和母亲的传递中,感应着我们的深处,我们顺应着行走。
1984年,母亲送走了外祖母后,来到了我和父亲的身边。我还是眷恋着生我养我的故乡。我有时间就独自回去看看,那时大伯母还在。每次回去我都会给伯母手里塞点钱,虽然那时伯母的眼睛已经有点看不见了,我只是为了让伯母拿在手里高兴高兴而已。我的所做也不曾告诉父母亲。父亲告诫过我:“有了条件不要忘了疼爱过你的人,帮就帮比你穷的,十元钱有可能让她们度过难关”。这就是父亲!
父亲对我别的方面的要求不比母亲宽容。我们的大院里住着八户人家,父亲是老住户了。平时,父亲从来不让我随便串门子,只是过年的时候,挨家挨户拜个年。平时我更不能穿着拖鞋,穿着毛裤出入屋外和院外,不允许买化妆品。老古板的我,在父亲的严教下,这块土坷垃在八十年代就很开放的城市里,若干年里都没有被风化。
我的改变是从父亲对我的又一次奢侈中得到。1985年,父亲为我买了一台天津产的牡丹牌缝纫机。父亲除了喜爱绘画,还喜欢服装设计,父亲把希望寄托在了我身上,可我对绘画一点灵感都没有。父亲就让我在工作之余自学起了服装裁剪。父亲的衣服有的是自己设计,自己缝制的,这么多年都没舍得买缝纫机。父亲把时光和爱给了家庭,给了孩子,舍弃了自己的酷爱。父亲保留的唯一一幅山水画,一直挂墙壁上。工笔画我也只见过两张,一张是给祖父放大的遗像,一张是为李伯伯的父亲放大的遗像。不过,后来我听伯家大姐提起过,早年看到过父亲画过周璇、王丹风、赵丹等人的画像, 据姐姐说棒及了。在我跟父亲的一次聊天中,我为父亲感到惋惜。父亲说:“没有什么可遗憾的” 。这就是父亲 !
我有了女儿后,父亲象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对我女儿的疼爱,提升到了逆爱的成度。从那时起,因为孩子,我和父亲间不断地发生矫情。过去,看到别人家的孩子,因满足不了的愿望在大街上而哭着撒泼时,父亲回到家就放肝气。不过我女儿在我父亲面前没撒过泼。因为孩子有求必应,父亲也不管孩子的要求合理不合理,也忘记了他为别人逆爱孩子而不满,更忘记了他对育儿的条规。

父亲对隔辈人的溺爱,只表现在我女儿的身上而已。
记得很早以前,父亲回家过年。大姐的两个儿子都来了。二杰看到桌上放着两瓶水果罐头,说:“老爷我想吃罐头”。“等你哥哥醒了一起吃”。大杰因感冒睡着了。“老爷那不是有两个么”,孩子话音刚落,就因孩子犟了一句嘴,父亲的暴脾气,愣是把罐头摔在了地上。大姐家那时的条件就已很好了,孩子并不缺嘴吃,可能是见到老爷撒娇的缘故。我们姐仨也给父亲宠惯了,谁敢在父亲面前说个不字。发生了这一幕后,孩子乖乖地上炕睡着了。醒来的第一句话:“老爷我要回家。”于是我冒着大雪,背着二杰送回了家。不过,这次我有点埋怨了父亲。过了两年,也就是我到天津后的第二年,我回家时把二杰带到了天津,父亲炖出了红烧肘子,把一个大大的肘子放在了二杰的面前:“快吃吧,尝尝老爷做的好吃不”。不过,第一件事给我留下了话柄,看到他宠我的女儿时,我就揭父亲的老底:“您为什么不象管教二杰那样管教茜茜”。尽管我这样问父亲,父亲也没有了脾气,不过在茜茜身上还是我行我素。

1990年的时候,我家的平房拆迁。父亲和母亲暂时回了老家。后来听母亲说,回到家又犯老脾气。老拿过去的老黄历,来约束现在一家一个的宝贝。开始给我二姐的儿子小辉立规矩,孩子到了那里吃点动西,不跟父亲打招呼,父亲就开始发脾气,在一些事情上横挑鼻子竖挑眼。那时,小辉也就是刚刚懂事。小辉在不到一岁的时候,姐姐把他送到了父母亲和我的身边。那时 ,父亲白天上班,半夜里还要亲自起来给小辉热牛奶 。我们姐仨小时候很少在父亲身边待过。其实,父亲的心里别提有多喜欢小孩子了。这就是看似不近情的父亲。后来,父亲返回天津,有时给我女儿买东西,无意识中就买成了双份。母亲就会笑着说:“小辉在老家呢”。
1997年,父亲有点脑梗,腿脚不太灵便,大姐把父母接回了老家。天有不测风云,2005年,大姐因病早早撒手人寰。大姐走后,二姐把父母从家里搬到了隔街自己家的后屋。转年,我又回去看望年迈的父母。好多年没守在父亲膝下了。在短短的二十天里,我形影不离地陪伴在父亲的身边。有一天,从小没緖摸过父亲的我,心血来潮中跟父亲开了个玩笑:“爹,您的钱呢,给我来点吧!”我闯祸了,严厉的父亲第一次跟我发威,大声地喊“走”。我是不应该撒娇了,我带着悔过的泪跑到了二姐的前屋。这时,母亲随我过来了,母亲说:“他老糊涂了,别往心里去”。我回到了父亲身边:“爹,别跟我生气啊!”父亲没再说话。母亲开了腔:“你老糊涂了,孩子什么时候找你要过钱”。其实,从大姐走后,我每月都往家里寄钱,来弥补着我出门在外的不孝。我没让二姐告诉父亲,就连母亲也不知道。我知道这弥补不了父母的生育之恩。不过我还是就此机会,让母亲把父母一生不多的积蓄交到了二姐手里。同时,把所有的重担留给了二姐。母亲已经老了,没有能力再去采买了。
这个外钢内柔的父亲,有时,在我们面前向来不露他内柔的一面。母亲告诉我,搬到二姐后院后,每天晚上,父亲看到二姐屋子里亮起灯,知道姐姐下班了,父亲才肯上炕休息。这份父爱越老越浓,母亲不说,我们都不知道。
父亲的病,在母亲细心的照料中,病情没有发展。母亲每天晚上都要给父亲泡脚,然后再用按摩机按摩,十年如一日。少是夫妻,两地分;老来老伴,老来哀!不幸再一次降临在年迈的父亲身上。照顾了他十一年,跟他过了一辈子没有一句怨言的母亲,在牵挂中离他而去。送母亲的那天,我让哥哥们把父亲搀扶下地,让他最后看了一眼母亲的遗像,父亲流着泪,象孩子一样哭了。送走母亲后,父亲糊涂了。多年不见的人,父亲依然认识,可就是一直在找母亲,天天在问:“你娘呢,你娘呢”。看到父亲这个样,我心里酸楚楚的。
给母亲上完了三七坟,我回了津。走时,我和二姐定好了,转年清明节我再回去。没想到两界之隔来的就那么突然,突然的令我回不过神来,我牵着父亲的手,泪如泉涌。父亲去了,在儿女们的泪水相送中永远地去了。
亲爱的父亲,我爱您!我用拙笔伴着泪水写下了您平凡中的琐碎。思念化作春泥伴我渐行渐远……
牛力拉车洒汗泉,奔劳食草吐汁艰。
辛苦甘为辛苦尽,泪泛悲声恩未还。
仅此献给天堂的父亲和我的孩子们
于2018年6(父亲节前)修改于2019年10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