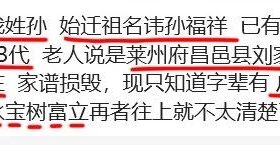上世纪1970年代,在我们家乡是一个地瓜的年代:人们大面积种着地瓜,大半年吃着地瓜。春天农耕伊始,人们便开始了地瓜的种、管、收、晒、储……一年三季,可以看到田野里到处都是地瓜,地瓜多的令人厌烦,可地瓜在饥饿面前,成为我们胶莱河谷地老百姓的救命“恩人”。

对有的人来说,地瓜确实不好吃。夏兰恩奶奶吃够了煮地瓜,干够了地瓜活,于是看累了地瓜,称地瓜是“敌人”!可为了活命,人们还得好好伺候“敌人”。每家每户都要在房前屋后空闲处挖一口地瓜井子,生产队要掘一口连一口成片的地瓜井子,待到秋天储存新鲜地瓜,留做冬天和来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吃,并备作地瓜苗种。地瓜井子不如现在姜井深大,有三、四米深,不用砖砌,在竖井壁两侧各挖几个窝,我们小孩就可以左右踩着,上下自如拿地瓜。由于地瓜井子口小,下井子拿地瓜成了我们小孩子的“专利”,我们在井下洞里装地瓜,大人在上面拔。地瓜装满了,就用手扶着桶,向上喊一声:“好了~ ”大人听到后,慢慢向上拔去。如果一不小心,就会被桶里掉下地瓜砸着头顶。所以拿地瓜,需要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密切配合。

这样不大的井口,多是用厚重的废旧石磨盖住,既省钱又牢靠。如果地瓜井子盖的时间久了,特别是出现地瓜腐烂,井子里就会缺氧,这时候冒然下井子,会闹出人命来。为了保证安全,下井子前,我们会打开井盖通一会儿风,再找来照明用的煤油灯点燃,用罐绳慢慢地往下续,直到地瓜井底,看看灯会不会灭,如果灭了,就是缺氧,是不能下去的。这样检验井子里氧气浓度的方法,就地取材,简单易行,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多么伟大!
入冬开始直到春天,地瓜成为老百姓的主食,人们大都依靠吃地瓜度日。因为小麦、玉米少的可怜,需要留作“三夏”和“三秋”大忙季节吃,有一年我们队每人才分70斤小麦!人们不是不想种,而是不能种。小麦、玉米产量低,解决不了人们的温饱问题,在“吃饱”和“吃好”的问题上,不得不首先选择“吃饱”。吃地瓜还有一样好处:“地瓜不耳咸菜。”人们如是说,是指吃地瓜不用就咸菜。每年春天,都有一些家庭连咸菜都不够吃,因为我有时看见母亲给本街上困难的家庭送去咸菜。对这些家庭来说,吃地瓜又是一份难得的节约。
隆冬时日,家家户户就会每隔几天煮一大锅地瓜,锅的中央还要放一黑泥瓦盆水,留作吃饭时饮用,可以节约烧水柴草。大人们就是这样事事处处节约,精打细算。有一位大爷要求孩子们吃地瓜不扒地瓜皮,让我想起了唐朝诗人李绅的《悯农》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点点滴滴、一草一木都是辛勤的付出。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,不当家不知道油盐柴米贵,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,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。”(《朱子家训》)
冬天吃地瓜,老百姓还有“吃顾地瓜”一说,就是辛辛苦苦劳累了一年,农闲了,难得吃地瓜不用干活了。这样,人们开始了“偎冬”—-许多人,多是妇女儿童,冬天围坐在炕头上,相互依偎着,把腿脚伸到炕中间麦瓤包底下取暖,讲述着民间传说和身边的奇人趣事,偶尔穿插着哼唱一段地方小戏—-“地瓜戏”,其乐融融……裹着发髻的姥娘坐在炕下的条凳上,一边编着地毯不语,一边听着她们的故事,至故事热闹深处,也会抿嘴一笑。

像现在仍有一些老人一提地瓜就口吐酸水厌恶地瓜一样,我母亲不喜欢吃地瓜,我家里煮的所谓地瓜都是些小地瓜、地瓜根子之类的喂猪用,根本没有我喜欢吃的。我常常羡慕同学葛方同家,他家每次煮的地瓜都是大小匀和、明正没地蛆眼的,好看好吃。每每看到他们大锅一敞,他急牢牢地撮起地瓜,先掰掉地瓜把,又一片片揭掉地瓜皮,在冬日暖阳光线下,热气缭绕,露出沙蜜蜜的黄瓤时,馋的口水都流了下来……也许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吃着地瓜长大的,并不为过。
地瓜种多了,单纯依靠地瓜井储存是不够的,春天过后地瓜会发芽变质,所以大量的地瓜在秋收时要切成地瓜干晾晒,成为地瓜干储存。深秋霜降前,生产队白天集中人力出地瓜,晚上直接在地瓜地里各户抓阄排序分地瓜,省去了运输回村的麻烦,不但省工省力,又有场地晾晒瓜干。大人白天劳累一天,一到晚上还要马不停蹄,挑着灯笼,推着车子,领着我们这些半大孩子,滴流哒哒,去擦地瓜干。大人负责擦地瓜干,我们就管着在刚出过地瓜的地里用耙子简单地一搂,保留小块坷垃,在上面摆上地瓜干,好透风晒的快。我妹妹和堂妹葛正华这些不懂事的小孩没人照看,也被带到现场,晚上困了,就用棉袄包一包,睡在车子上的偏篓里。我们人小晚上摆不完就打盹了,第二天一早还要再去接着摆。

地瓜就这样不停地白天出、晚上擦,遇到雨天也是常有的事。当时的天气预报没有现在的准确,于是人们戏说:昌邑县“约摸站”(广播站)、一天三时浪费电。晒地瓜干靠运气,遇上下雨,还要抢拾晒得半干不湿的地瓜干,不然就会烂在地里。实在没有办法,对于淋湿变质的地瓜干,只能用来换酒喝,当然是过年过节给客人喝,摆上一瓶县酒厂出的“串香”高度白酒,就是对客人最大的敬重。抢回来的地瓜干要逐叶割口,上下一排排整齐地挂在屋檐下、大树间横拉的细铁条上,慢慢晾干。遇急雨一般要先抢拾大的地瓜干,做到“捡西瓜丢芝麻”。可有一位叔叔嘱咐孩子,下雨抢拾地瓜干要先拾小的。为什么?—-小地瓜干容易碾进泥土里去。这位叔叔的独特“理论”虽一时为乡里爷们所耻笑,但也不无一定道理。
地瓜难吃,晒地瓜干又如此费心耗力,勿怪乎夏兰恩奶奶说地瓜就是“敌人”了!但正是“敌人”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拯救了我们:它不嫌土地,产量高,而且叶梗可以做菜吃,连蔓子都可以喂猪喂牛,全身都是宝,是它把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拉了回来。

过去充饥解饿的地瓜,现在或蒸或烤,或做成地瓜“棋子”,沿街移动叫卖,超市专柜销售,甚至成为馈赠客人的佳品,登上了大雅之堂。这才是:生蔓截栽耐土薄,香甜可口用途多。灾荒年月充饥馑,富裕之秋进礼盒(拙作《七绝·甘薯》)。